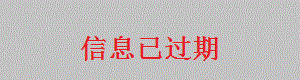
当北方的雪一个接一个的覆盖了时间的裂缝,你等待的人会不会长途跋涉回来?
我居住的城市,冬天漫长而寒冷,却以其独特的姿态让常年居住在这里的人怀念和习惯。
我周围的大多数人都不喜欢冬天,因为太冷了。我对冬天有着持久的偏好。
记忆中的冬天,是大街小巷地瓜小贩的叫卖声,是热气腾腾的糖炒栗子,是妈妈永远织不完的毛衣。吃完饭,我一边吃红薯一边坐在火边,一边帮妈妈把腿上的毛线梳到手上,然后卷成精致的小毛球。我妈总觉得我拿红薯的手弄脏了她的毛线,所以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我爸就来接替我的工作。他厚实的手掌上五颜六色的线球,零星的老茧变得灵动而有规律,他妈妈的嘴巴也会悄然上扬。我看着窗外。院子里的雪还没有融化。雪花在空中飞舞。在通往村口的小路上,一些脚印,或深或浅,慢慢被雪花覆盖。不时有几只狗吠叫,伴随着父母商量购买年货的声音,画面温馨安静。
这样的场景在我脑海里根深蒂固,以至于很多年后,我依然清晰地记得妈妈教给我的每一种编织方法,还有指尖扎针的痛苦,但那条一直没织完的围巾,早已被我遗忘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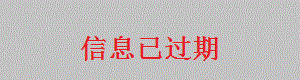
再后来,每到冬天,对我来说,开心的事就少了。红薯不再甜了,家里也没人穿我妈织的毛衣。炉火周围的剪影渐渐变成了两个无声的等待背景。从那以后,我再也没有完整地在家乡度过冬天。
那条我们走了无数遍,通向村口的小路,在漫长的岁月里,陪伴着父母等待游子归来,以最虔诚的姿态伫立。在这条路上,当我们重逢时,笑着,哭着,离别时,吵着,还是冷着,它只是静静地问候我们,一次又一次问候我们,迈着欢快的,沉重的,或者不甘的步子。这条路对于村里的人来说不是一条简单的路,而是承载着所有无法表达、无法跟随、无法陪伴的沉重的思想。
即使离开村子很多年了,每年有时间回去的时候都会停下来走那条路。回头看,路上还是有孩子在来回跑。往前看,有几对老人依偎在一起,看着远方,我站在他们中间,仿佛我是一个陌生人,像昨天一样。
在这条路上,我看到了曾经郁郁葱葱,现在已经荒芜的菜园。
只见东方,一直坐在门口发呆的两个老人,现在只剩下一个摇摇晃晃的身影。
看到角落里最著名的黑猫,蜷缩着,半眯着眼睛,舔着零星的白发。
看到奔跑的孩子,盯着远处的老人,笑着朝一个方向走去——他们等待的人回来了。
知道每一次短暂的见面之后,都是可预见的未来的等待。远方归来的人纷纷踏上征途,留下的人继续在这条通往村口的寂寞路上徘徊。他们都在等待,等待来年的雪融化,等待小麦一次次的成熟,等待孩子被冻得面红耳赤,等待又一年的大雪,然后等待的人就会出现在路的另一端,从模糊的形状到清澈的体温,一点一点的填补彼此的思念和融化。然后再等,看着他们的背影渐行渐远,再次消失。
就像龙应台在《守望》里说的:我慢慢地慢慢地明白了,所谓的父女母之事,只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,就是这辈子一直看着他远去。你站在小路的这一头,看着他在小路的转弯处渐渐消失,他背着你默默的告诉你:别追了。
相关阅读
标签: #年关将至弥勒飞机场最新动态










